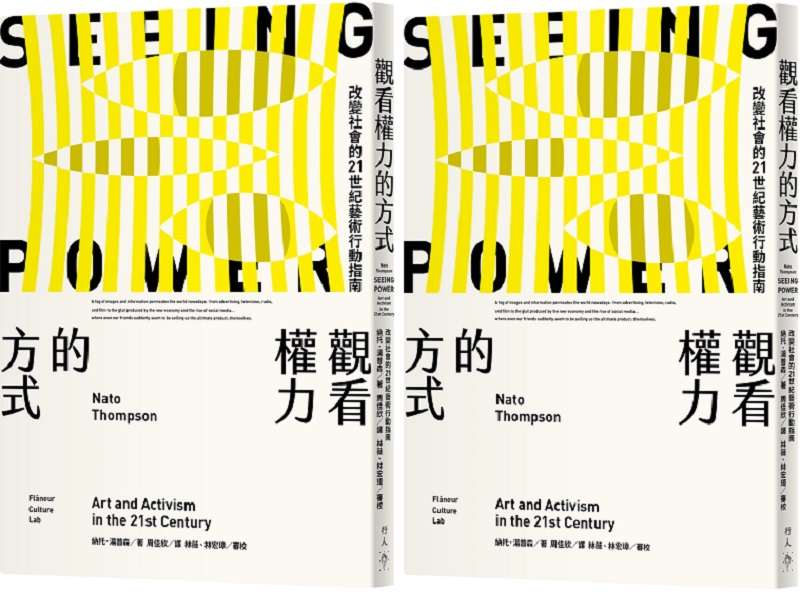經濟的巨幅改變,已經對構成藝術的事物造成深刻的衝擊。歷來的藝術家回應著自己生活的時代,而在20世紀初期用來構成藝術的工具,諸如影像創作、表演、設計與建築,在當今的廣告界和媒體界裡則是基本的技巧。事實上,相較於創意產業的規模和範疇,藝術家的創作顯得相形見絀。這就意味著,想要衝破文化生產的陰霾時,藝術家必須更加足智多謀,而這並不是個簡單的任務。
在全球各地自認為是藝術家、藝廊、博物館、雜誌和藝術學校的複雜配置,如此龐大而多樣,以至於無法一概而論—至少我並不打算這麼做。我在本書裡聚焦的,是那些自覺地在藝術與政治的交匯處操作的藝術家。即使在這樣的資格限定之下,我們仍需要做一些歸納。從20世紀晚期到21世紀的頭20年,我們見證了國際藝術界的興起,其中,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這個無所不包的詞彙,取代了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用於描繪數不勝數的美學風格與歷史,它們橫跨國際藝術創作的廣大光譜,相互接連、碰撞與結合。整個1990年代,雙年展開始在全球各個城市興起,從廣州、伊斯坦堡到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隨著這個藝術邁向國際展覽的取向盛行,隨之而來的就是助長當代藝術市場和藝術本身的大量資金。
然而,我已經提過,儘管本書意識到雙年展的激增和新全球藝術市場的崛起,但書中特別關注的是作品觸碰到藝術與政治交集的藝術家。儘管這些藝術家之中,有些確實與市場的基礎結構和收益流量相互牽動(確實是如此,即使是非商業性藝術的論述與空間,也無法全然不受巨額融資的藝術市場的影響),但這些藝術家創作時所處的環境,有著格外獨特的軌跡。
關注人群與社會的行動藝術 社會美學啟動結構連結
其中特別要提及2個突出的藝術生產,這2者是重要先例,影響了近來大多數的藝術和政治工作:社會美學(social aesthetics)與戰術媒介(tactical media)。社會美學關注的是人(因此是透過人而生的政治),而戰術媒介則只將藝術視為擾亂權力的工具。社會美學多半與行動主義的關係較不明顯,而戰術媒介則是擁抱自身昭然若揭的行動主義基礎。這是2股不同的藝術運動,但都感興趣於把藝術帶進整個世界,並使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訴說。正是這個共同的取向,使得這2個路徑對理解現今運作中的藝術與政治至關重要。
社會美學興起於1990年代中期。此時,藝術一下子變得更側重社會性和人際關係,毫不懼怕無形與即時的呈現。這是行動的藝術。這是涉及人群的藝術,且並非總是發生在博物館裡。這種藝術創作者的靈感來自於對大眾文化的高度質疑感受,故而強調的是即時的、個人的以及有時是政治性的層面。 (相關報導: 這就是我們的天性:《白銀、刀劍與石頭:魔幻土地上的三道枷鎖》書摘(5) | 更多文章 )
社會美學強調的人際關係,往往發生於博物館或藝廊的環境之外。這是關注社會性的藝術。以「住屋者網絡(Tenantspin)」為例,它是丹麥藝術團體「超柔(Superflex)」於2001年的創作,地點是英格蘭利物浦的一處公共住宅大樓區。超伸展的藝術家運用網路播映技術(Skype當時還未發明出來)發展出了一個媒體頻道,供住民討論發生在住宅社區裡大小事。不論關心的問題是租金、待修設施、在地烘焙義賣,甚或是即將到來的卡拉OK聚會,「住屋者網絡」都是作為公民活動的觸媒而運作。沒有當地住民的互動,這件作品就不會存在。就本質來說,啟動社會性的事物就是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