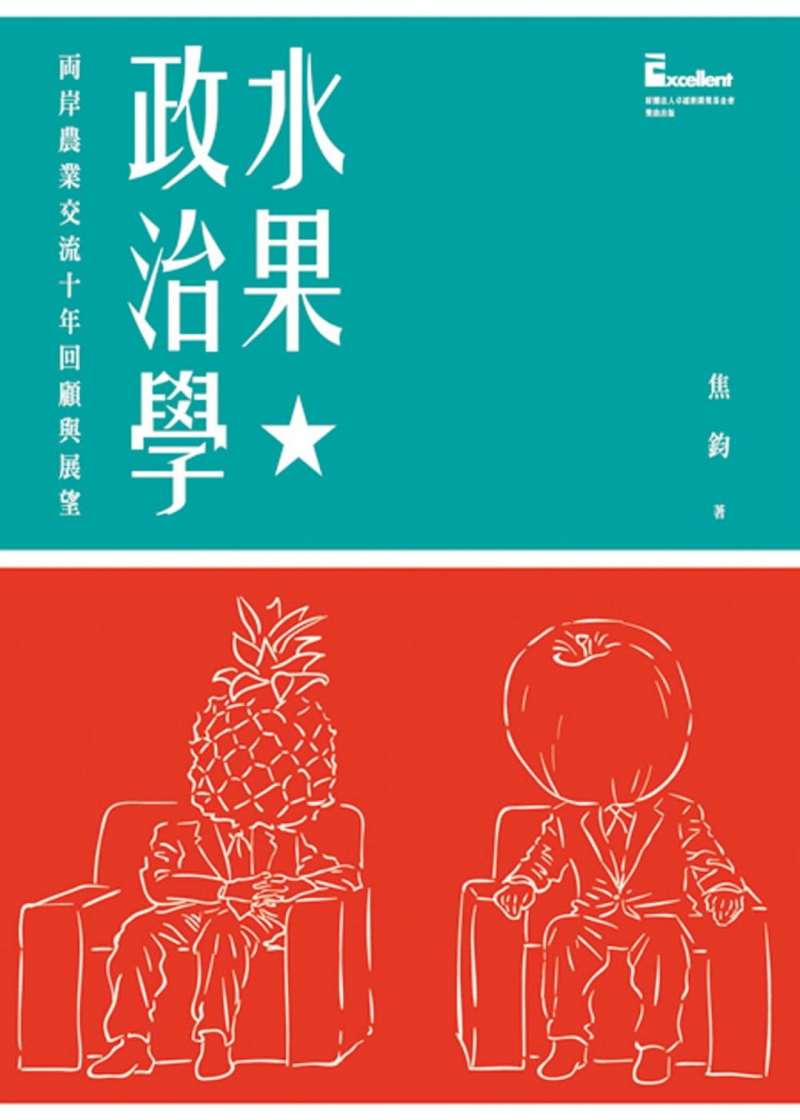農會依據《農會法》行事,農會系統則繼承自日據時期的農民合作協同組合,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以及臺灣,都設有農會組織,提供農民服務。
以日本為例,日本全農(JA)相當於「中華民國農會」(簡稱全國農會,由過去的臺灣省農會改制升格而成),日本的縣農會則與臺灣的各縣市農會相當。臺灣目前歷史最悠久的農會是新北市三峽區農會,成立於日據時代西元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九月的「臺北三角湧組合」。
農會主要的任務是服務農民,依《農會法》規範,主要工作為推廣、供銷、信用、保險等四大功能。
農會的領導階層為理事會、監事會,理事長對外代表農會,監事會則選舉出常務監事;至於日常的會務治理工作,則由總幹事負責。由於臺灣各地農會生態不同,一般來說北部地區多由理事長掌權,中南部地區則為總幹事為首。在農會選舉的制度設計上,理事長為間接選舉產生,由理事之間互選理事長,且其為無給職;總幹事屬聘任人員,由理事長提名到理事會通過後任命。
過去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密切,農會員工也多與此有關;如今制度化之後,農會員工多以統一招考分發之。即使農會員工招考晉任制度化之後,各級農、漁會的權力掌握者仍對地方派系有運籌帷幄的實質影響力。
農會龍頭「理事長」的位置有多重要?一般民眾對此了解的不多,但可能偶爾會在社會版新聞看到「農會理事長涉嫌賄選遭羈押」的新聞;這個情況,在國民黨一黨獨大,農會作為國民黨組織系統底下的一個「組織運作」的年代,尤為明顯。
間接選舉制度往往贏者全拿,這也是農會理、監事選舉時,往往形成不同派系間廝殺的原因,進而遭地方派系或特定人士的操控壟斷。農會理監事選舉的「綁樁」花費極大,花招也極多,除了經費要充足之外,沒有一定地方實力者也甚難擺平其他勢力的競逐,當然這些都是地方派系的強項;魚幫水、水幫魚之下,農會很難脫離地方派系的勢力範圍。
之前提到了陪同許信良出席的幾位關鍵人士,包括當時的臺灣省農會理事長古源俊、曾任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理事長的雲林縣農會理事長謝永輝、在國民黨智庫任職的農民詩人詹澈等人,都是二○○四年之前農業界檯面上的要角。
從宋楚瑜任臺灣省長時期的臺灣省農會理事長簡金卿,到李登輝凍省、民進黨執政後的臺灣省農會理事長古源俊,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簡金卿一九九六年曾任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同一年順利連任臺灣省農會理事長,不過卻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因案停職,最後由省農會理事、曾任彰化二林農會理事長的洪允闊代理。洪允闊代理期間,聘任二林農會總幹事謝國雇出任臺灣省農會總幹事,謝國雇後來轉任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副總經理、升任總經理一職,也是經常往來兩岸從事農業交流的活躍人物。
二○○五年臺灣省農會改選,古源俊不敵立委派,全面退出農會系統。古源俊的繼任者臺中縣紅派大老、立委劉銓忠,結合國民黨全國不分區立委、曾任臺北縣農會理事長的白添枝,加上前雲林縣長張榮味的妹婿張永成,形成臺灣省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總幹事」鐵三角,立委派大獲全勝。
自此之後,省農會歸於「大一統」,也鮮少在社會新聞版面出現有關「暴力賄選」的負面新聞。
這些參與理監事選舉的農民代表,其實都只是幕後操盤手總幹事的「人頭」;總幹事在理事會改選前沒有掌握過半席次,自己的聘任就過不了理事會這一關。競爭激烈的農會選舉多採「2:1:7」的方式,要搭檔競選農會三長的人依上述比例認列「競選經費」。
不過,農會理事長才是農會的法人代表,各種對外事務也多由理事長代表出面,出訪中國大陸交流這等要事,理事長一定是親自出席;「出訪」同時順道安排「出遊」,招待這些地方要角理事長們,也成為日後兩岸農業交流的一個潛規則。
謝永輝理事長則一直活躍於農業界,爾後在兩岸農業交流的舞臺上,因緣際會成為「台灣農民黨」黨主席,也在兩岸間扮演非常重要的「農業大老」角色。
與農民團體的關係進一步深化,緣起於立法院工作時的老闆:前立委白添枝。
二○○五年臺灣省農會理監事選舉延宕,扁政府時期的農委會輔導處,刻意以公文流程來技術性干擾選舉時程的進行,但是在有意角逐臺灣省農會理事長的臺中縣區域立委劉銓忠、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白添枝,以及有意擔任省農會總幹事張永成的立委夫人張麗善,聯手向農委會抗議,才順利讓古源俊交出臺灣省農會理事長位置。
臺灣省農會是否真的可以代表全臺灣農民?就《農會法》的精神,農民加入農會成為會員,可以享有農會的服務,與申請其他相關的政府補助款項,最重要的就是「農民保險」身分的確認。因此,農民一定是農會會員,但農會會員未必就是農民;這一點,媒體經常報導的農地非農用、農地遭炒作等,道理就在此。但取得臺灣省農會三巨頭的身分,就等於對外取得全臺灣農民代言人的角色,這是法律所賦予的實質權力。
白添枝在與劉銓忠競爭省農會理事長失利之後,經「協調」轉任臺灣省農會常務監事。在二○○五年中確定臺灣省農會的改選日期之後,來自全國各縣市農會理事長,在國民黨黨政高層的授意下,齊聚高雄縣農會商討此次臺灣省農會理、監事改選的席次分配問題。
這樣的組合,也開啟了以立委主導農會體系的時代,讓農會的實質政治影響力日增,當然也使得農會高層與國民黨的權力核心,處在一種微妙的關係。
馬英九接任黨主席後,二○○七年的國民黨全國不分區立委名單,並沒有依著連戰時代的老習慣,安插至少一名農會界代表,白添枝因此失去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舞臺,連臺灣省農會常務監事的位置都岌岌可危。當然,馬英九極力改造國民黨,想與地方派系的「黑金」切割,也讓部分農會大老憂心忡忡。
因為在立法院擔任助理,也就被授意進行「組黨準備」。最後一刻,國民黨提名了張嘉郡,繼承了她的姑姑張麗善的選區,繼續披掛藍旗參選;但此時,幾位主戰派的農會大老,認為組黨工作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跳開農會系統的幾個大老不說,基層農會並不全然認同「脫離國民黨」的做法;而當初名列發起人的一些重量級農會領導人,到最後籌組階段也斷然鬆手。
最後搞到弄假成真,主要和當時臺灣政壇在二○○八年第七屆立委選舉席次減半,首次實施不分區立委採計第二張政黨票的社會氛圍有關。最後農會系統部分大老發起成立「台灣農民黨」,與當時其他政黨,像是第三社會黨、紅黨、人民火大黨等,均跨過中選會門檻規定的在區域立委登記超過十名候選人,可以列入政黨票,搶奪不分區立委席次。
因為臺灣省農會的實質退出,整個組黨工作落在當時高雄縣農會秘書蕭漢俊身上;加上當時未獲國民黨提名的新竹市區域立委柯俊雄,加上當時臺北市農會總幹事錢小鳳、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理長潘連周、臺鐵工會理事長張文政等人共襄盛舉,台灣農民黨也一如其他新成立的小黨,推舉出自己的不分區立委名單。
台灣農民黨的黨主席,則由謝永輝先生以農業大老身分出任;他明知這麼做絕對換不到國民黨關愛眼神,反而會遭致國民黨的挾怨報復,仍義無反顧地扛起這個政黨的存續。
一如預期,這幾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小黨,大家都沒有跨過二○○八年立委選舉的政黨票百分之五門檻。結束了一場政治操作,選舉結束後也短暫的休息、沉澱;但也因為台灣農民黨的籌組過程,才有機會有規劃性地走入嘉義農村半個月,實地體會菜農、稻農、豬農的辛勞,並聽見他們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