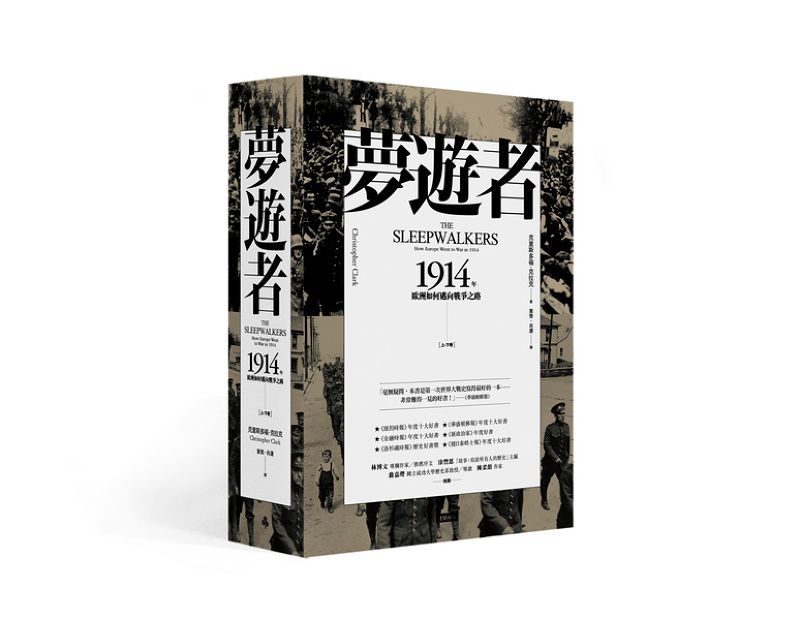二十世紀初歐洲盛行君主制。六大列強之中,有五個具有不同形式的的君主政體,只有法蘭西共和國是例外。巴爾幹半島新成立的民族國家,如希臘、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全都是君主政體。但擁有快速巡邏艇、無線電報機和雪茄打火機的歐洲,卻仍然沿襲古老而輝煌的體制,將龐大且複雜的國家與人類生物學的奇異想法結合在一起。歐洲的行政官吏仍然將王權和王室視為施政重點。德國、奧匈帝國,以及俄國的大臣都是由皇帝欽點。三大帝國的皇帝都有無限制干涉媒體的權力。同樣的,他們對於軍隊都有統帥權。國家之間的溝通是以皇朝的體制來實現。
英德俄的3位表兄弟君王
戰前歐洲的君主體系代表人物是三位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和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對每位君主在其治理地區的影響力進行評估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英國、德國和俄國,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君主制。俄國的君主制是絕對獨裁,其議會和憲法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十分微弱;愛德華七世和喬治五世代表的是立憲和議會君主制,他們沒有直接操控國家的權力;而德皇威廉二世則介於兩者之間。在德國,立憲和議會體制被嫁接到舊有的普魯士軍事君主制中,後者由於歷經國家的統一過程而被保留下來。但是統治架構的決定性因素並非在於君主施加的影響力,其他重要的因素還包括君主本人的決策能力和洞察力、大臣對異議的控制能力,以及君主與其政府之間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達成共識。
君主造成的重要影響中,最顯著的是外交政策隨時間而變動。負責一九○四至一九○七年外交改組的愛德華七世,對外交政策有很強的自我觀點,並且對自己能充分了解資訊很自豪。他的態度是帝國「沙文主義」的代表,例如,他很惱火自由黨反對一八七八至一八七九年的阿富汗戰爭,於是向殖民地行政負責人亨利.巴圖.費里爾爵士(Sir Henry BartleFrere)說:「在我們尚未完全擁有阿富汗之前,我是不會滿意的。」對一八九五年突襲川斯瓦共和國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他非常欣賞和支持塞西爾.羅德斯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但是對德皇的「克魯格電報」卻十分惱怒。他成年後一直是堅定的反德人士,這種反德情緒部分來自他對母親維多利亞女王的反抗,他認為母親對普魯士過分友好,部分原因是他對不苟言笑的德國教師史督曼男爵BaronStockmar)的畏懼和憎恨,這位教師是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安排,目的是讓年輕的愛德華能夠熱衷學習並終身學習。一八六四年普魯士和丹麥爆發戰爭,對於這場戰爭,愛德華同情剛迎娶的新娘的丹麥親人。愛德華繼任後,成為以法蘭西斯.伯蒂為首的反德團體的重要擁護者。
一九○三年,愛德華國王出訪巴黎,這時他的影響力達到巔峰,成為「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皇家來訪」,他為兩大敵對帝國建立協約關係的可能性。由於法國不支持波耳戰爭,兩大西方帝國之間的關係在當時仍不樂觀。這次出訪是愛德華的主意,並緩和雙方緊張的氣氛。與法國簽署條約後,愛德華繼續試圖與俄國達成共識。儘管如此,他還是很厭惡沙皇奉行的政治制度,並且對俄國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部署存有疑慮。一九○六年,愛德華聽說俄國外交大臣伊茲沃爾斯基在巴黎,他便從蘇格蘭一路南下,只為了會晤伊茲沃爾斯基。伊茲沃爾斯基對此也做出友善回應,動身來到倫敦。根據查理斯.哈丁的描述,兩人的談話「在實質上為英國與俄國達成共識奠定了基礎」。上述兩個例子顯示,國王並沒有動用過多的行政權,反而像是一位「編制外」的大使。愛德華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與白廳的自由帝國主義派系緊密結合,而這些主導外交政策的派系成員,也是他不遺餘力支持的人。
喬治五世則是相反的例子。他在一九一○年繼任前,對外交事務並不感興趣,英國與其他列強之間的關係,他也只有概略的印象。奧匈帝國的奧地利大使門思多夫伯爵(CountMensdorff)對這位新國王十分滿意;與他的父王相反,這位新國王對任何支持或是反對的國家都沒有強烈的偏見。如果門思多夫希望新國王登基能夠降低英國政策中的反德成分,那麼恐怕不久後他就要失望了。在外交政策,喬治五世看似中立的立場僅意味著,決策權緊握在以格雷為首的自由帝國主義者手中。喬治五世從未籌組與其父王相抗衡的政治派系,他受到許多政治勢力的牽制,在沒有徵求大臣的意見前他不能對政策做出決定。喬治五世會與格雷保持聯繫,在與外國代表進行政治會晤時,他會尋求格雷的意見,尤其對方是德國人的時候。
雖然幾個歐洲國家君主是表兄弟,但最後仍搞到兵戎相見。
因此,喬治五世的繼任使得王室無法主導外交政策,儘管憲法規定兩位君主擁有相同的權力。在俄國,其獨裁統治呈現高度集權化,但沙皇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也是受限,只是隨時間變化受限程度不一。跟喬治五世一樣,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八九四年繼任時也是一張白紙,沒有任何經驗;成為沙皇之前,他沒有組織自己的政治黨羽,對父王的順從也使他在表達對政策的意見時受到重重阻礙。還是青春少年的尼古拉二世,並沒有展現學習國家事務的天賦。保守派法學家康斯坦丁.波別多諾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曾被選為指導小尼古拉,如何處理俄國內部政務的教師,他回憶:「我唯一能觀察到的就是他全神貫注的挖鼻孔。」即使加冕後,他的極端靦腆和對展現政治影響力的恐懼,使他在早年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行事。此外,他缺乏執行力,無法持續形成政策路線。而且他沒有個人祕書。雖然他能獲得非常細節的部門決策資訊,但像俄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尼古拉二世無法對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出決定。
即便如此,尼古拉二世還是能左右俄國外交政策的具體動向,尤其是一九○○年前後期間。十九世紀九○年代末,俄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滲透。但領導階層並不是所有人都滿意這項遠東政策,有些人對巨額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軍事投入表示不滿;還有一些人,例如陸軍大臣亞歷克塞.庫羅帕特金(Aleksei A. Kuropatkin),則認為遠東政策分散俄國對西方主要地區的注意力,尤其消耗對巴爾幹地區和黑海海峽問題的精力。而尼古拉二世認為,俄國的未來不僅在塞爾維亞,還有遠東地區,最終支持遠東政策的人還是超過反對者。儘管最初有些擔心,但他還是對一八九八年奪取中國遼東半島旅順港的軍事計畫予以支持。在朝鮮問題,尼古拉二世支持軍方對該地區進行滲透,結果導致聖彼得堡和東京的利益衝突。
尼古拉二世對政策的干涉是以非正式聯盟的形式展開,而非循體制內管道來制定並執行決策。例如,他與貴族企業主保持密切關係,這些商人在朝鮮鴨綠江擁有林場特許權。鴨綠江林場的大資本家別佐布拉佐夫(A. M. Bezobrazov)以前是一名騎士,他憑藉與沙皇的私人關係,以鴨綠江為平臺,用非正式手段擴展俄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一九○一年,財政大臣賽吉.威特(Sergei Witte)表示,別佐布拉佐夫與沙皇「一週至少要見面兩次,見一次面就要談四小時」,為沙皇提供遠東政策的建議。大臣對這些在朝堂上舉無輕重的局外人的參與十分憤怒,但對他們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卻束手無措。在這種非正式關係的影響下,沙皇決策時變得越來越偏激。「我並不想要朝鮮,」一九○一年尼古拉二世對王子亨利說:「但我也不會允許日本長期待在那裡。這會成為開戰的理由。」
不久之後,尼古拉二世任命遠東總督以便加緊控制。總督不僅要負責遠東地區的民政和軍事,還要與日本斡旋。該機構的總負責人是亞歷西耶夫(E. I. Alekseev),他直接受命於沙皇,因此得以避開大臣意見的左右。這項任命是由別佐布拉佐夫為首的小團體策劃,他將此視為繞開外交部的手段。最終,俄國的帝國政策是在正式與非正式兩條平行軌道上展開,雙方相互競爭,尼古拉二世便可從中選擇。海軍上將亞歷西耶夫沒有外交經驗,對此也不甚了解,因此他不友善、固執的作風必然會與日本疏遠,甚至激怒對方。尼古拉二世是否明確的要對日本發動戰爭,我們無從知曉,但他必須對一九○四年的戰事及後續災難負最大責任。__日俄戰爭爆發前,沙皇的影響力十分強大,而大臣們卻一直遭到打壓。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為戰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讓他無法再主導一切。失敗的消息接踵而至,國內社會動盪不安,以賽吉.維特(Sergei Witte)為首的大臣提出聯合政府構想,並推動一系列改革措施。權力轉移到大臣會議手中,帝國第一次朝向主席或是總統的體制。在維特和他的繼任者史托里賓(P. A. Stolypin,一九○六至一九一一年)努力下,外交決策在某種程度上開始與沙皇的初衷背道而馳,反對進行侵略性的干涉外國事務。史托里賓是非常有決斷力、智慧和魅力,且勤奮的官員,他以個人能力打動大部分大臣,讓政府的權力提高,但在一九○五年之前,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史托里賓主導的幾年中,尼古拉二世「很奇怪的從各種政治活動中消失了」。
威廉二世是最具爭議
威廉二世是最具爭議的一位,他在德國高層中的權力也是後人爭論的焦點。德皇即位時確實有意讓自己成為外交政策的主導者:「外交部?我就是外交部!」「我是德國政策的唯一決定者!」他在一封寫給威爾斯王子(也就是未來的愛德華七世)的信中如是說,「我走到哪裡,我的王國就追隨我到哪裡」。威廉二世對大使的任命十分感興趣,常常無視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議,一意孤行。與其他兩位君主相比,他更將君主之間的會晤和通信視為帝國之間溝通的一部分,他認為這種獨特的外交手段對國家利益有好處。就像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尤其是在他早年執政時期)經常以自己的「偏好」避開相關部會大臣的建議,藉由助長派系之爭以破壞統一政府的形成,並且經常沒有告知相關部會首長就提出一些主張,有時這些主張還與現行的政策相矛盾。
就是這些作為以不具權威的身分提出未經認可的觀點,德皇因而招致眾人和歷史學者痛斥。不難想像,德皇對國內外政治議題的私人探討(電報、信件、提議、對話、採訪和演講)當中不乏一些古怪的論調和內容。這些獨特的想法十分引人注目,在他執政的三十年,可以說一直在演講、寫信、發電報、寫文章和進行批評,當中大部分內容為後世保留下來。其中有些意見既乏善可陳且不合時宜,這裡舉兩個例子,都與美國有關。一九○六年四月四日,威廉二世應邀到柏林的美國大使館作客,與東道主愉快交談過程中,德皇提到,為德國迅速成長的人口提供居住空間的必要性。他對大使說,他就職時的德國人口大約四千萬,現在應該成長到大約六千萬人。這本是好事,但他認為糧食問題是接下來二十年比較棘手的問題。此外,法國大部分地區出現人口不足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發展人口,或許應當詢問法國政府是否介意將他們的領土向西邊縮小一點,來接納德國過剩的人口。這些愚蠢的言談(我們只能將它視為笑話)被一位參與談話的大使館職員記錄下來,並裝入外交信件袋寄回華盛頓。另一個例子是發生在一九○八年十一月,當時外界傳聞美國和日本可能開戰,德皇獲悉後激動萬分,他正想討好美國人,於是十萬火急的致信羅斯福總統─這次是十分嚴肅的正式外交書信,表示願意派遣一支普魯士軍隊,駐紮在加利福尼亞海岸。
德皇的想法層出不窮,他先是對這些想法有三分鐘的熱度,每當厭惡或是受挫,又棄之如敝屣。也許這星期他對俄國沙皇氣憤不已,但一週後,這種態度可能又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對他來說,聯盟的計畫總是無窮無盡:與俄國和法國結盟,共同對抗日本和英國;與俄國、英國和法國結盟,共同對抗美國;與中國和美國結盟,共同對抗日本以及德奧義三帝國;或__是與日本和美國結盟對抗《英法協約》國︙︙一八九六年秋,當英德兩國關係在川斯瓦問題出現後降至冰點,德皇提議與法國和俄國達成同盟以實現共同防禦;就在同一時間,他又突發奇想,試圖放棄東非之外德國所有的殖民地,以消解與英國之間的潛在衝突。到了一八九七年春,威廉二世又捨棄這個想法,轉而認為德國應當與法國尋求親密關係。
威廉二世並不滿足於向大臣展示其思想成果,他還將這些想法直接傳達給外國代表。有時候他的干涉與官方政策相悖,有時又支持政策。一八九○年,德國外交部與法國的關係惡化,威廉二世又活躍起來。他的舉動與一九○五年摩洛哥危機時如出一轍,當外交部向巴黎不斷施壓時,威廉二世卻向幾位將軍和記者(包括一位法國前部長)保證,德國會與法國和睦相處,在摩洛哥問題上,德國無意發動戰爭;三月,就在他啟程前往丹吉爾之前,德皇在布萊梅發表演講,聲稱歷史的教訓已經讓他知道,「永遠不要在這個世界上追求無意義的權力」。此外他還表示,德意志帝國應當「作為一個冷靜、誠實和愛好和平的鄰居,贏得他國的完全信賴」。一些核心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鷹派的軍事指揮高層)則相信,這樣的言論完全是給摩洛哥官方添亂子。
一九○四年一月,威廉二世坐在比利時國王李奧波德(Leopold)旁邊(這位國王專程趕至柏林慶祝威廉二世生日),利用這個機會威廉二世對李奧波德說,假如德國與法國開戰,他希望比利時能夠站在德國這邊。威廉二世承諾,如果比利時國王支持德國,那麼比利時人將會獲得法國北部疆土,他也會授予比利時國王「舊勃艮第之王」的稱號。李奧波德大吃一驚的回答:他的大臣和比利時議會很難接受如此大膽的提議和幻想。威廉二世則反脣相譏,聲稱比起耶和華,他更無法尊重一個對大臣和副手負責的王室。如果不是比利時國王十分樂於助人,德皇將會「純粹根據戰略原則」採取行動,入侵並占領比利時。據說李奧波德對這一席話膽戰心驚,用餐結束後他站起身,頭盔都戴反了。
威廉二世的表達方式讓人十分不安,存在潛藏的危險,尤其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各個政府不斷揣度彼此的心思和意圖。然而,有兩方面我們不應該忽略。首先,在這種情況下,德皇的身分是領導者和控制者,而他卻不能真正改變什麼;其次,他言辭虛浮的恐嚇時常伴隨德國是受攻擊一方的假想。不能將威廉二世對比利時國王李奧波德不合適的提議理解為具進攻型的冒險行為,而應當看作德國面對法國外交攻勢的一種回應。奇怪的是,在未來發生的衝突中,他對比利時中立立場的破壞並非出於單純的破壞動機─法國和英國的參謀總長同樣對德國入侵比利時的行為進行研究和探討,我們應當在更大的環境背景下,根據雙方的地位特徵來看待這個問題。德皇的眾多特徵之一就是,他無法讓自己的行為合乎別人對他的期待。很多情況下,德皇並沒有像一名君王那樣發表談話,更像是一個熱衷於表達自己想法的未成年人。他是典型的愛德華統治時代宮廷的代表人物,即便是對旁邊的陌生人也會滔滔不絕的講一些生活瑣事,或是向同桌人講述自己最得意的計畫。難怪對當時歐洲許多政要來說,如果在午餐或晚餐時被德皇揪住不放而難以脫身,會是很可怕的事情。
威廉二世的為確實對德國外交部造成一定影響,但沒有對德國外交政策的方向起到決定性作用。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認識到自己無能為力且與真正的決策過程脫節,威廉二世才不停的表達自己的空想。例如後來發生日本和美國的戰爭、入侵波多黎各、全球針對大英帝國的戰爭風暴、將中國劃為自己的保護國,這些都是一名異想天開的人士按照自己的地緣政治思維勾畫的藍圖,並不是經由多方討論、嚴格審視下制定的政策。如果一場真正的衝突迫在眉睫,威廉二世會立刻偃旗息鼓,為德國尋求各方理解,解釋不發動戰爭的原因。一九○五年底,德國與法國的緊張關係劍拔弩張時,威廉二世驚慌失措的告訴比洛,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比國外的戰爭更值得關注;次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不期而來,與卸任的法國外交部長泰奧菲勒.德爾卡塞會面,這又讓威廉二世坐立難安,他告誡首相,德國的槍炮和海軍還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威廉二世只是嘴上逞強,但當麻煩真正來臨時,他卻百般試圖逃避。面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時,他確實按此原則行事。一九一二年五月,法國駐德國大使朱爾.康朋(Jules Cambon)在一封寫給法國外交部高官的信中說:「很奇怪,這個人如何能言語魯莽衝動,卻在行為上表現出謹慎和耐心。」
無論歐洲的君主是否對政治進行積極干預,但他們的存在的確是造成國際關係不穩定的因素。只有部分實行民主的君主體制呈現多樣的特徵,這些君主是被他們的執行機構所認可,他們能夠直接干涉國家的媒體和人事,並且對每項決策都有最終責任。純粹的外交政策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君主會參與重要的國家議題─毫無成果的比約克會晤便很好的證明。然而,外交官和政客(尤其是君主自己)將君主視為總舵手,以及國家政策的擬人化形象,他們的存在使得決策過程的核心一直處於不確定狀態。在這種意義上,國王和皇帝是國際關係混亂的根源。這種明顯的缺失讓各國都在努力建立明確和透明的外交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在所有地區的君主制度中發現相似的情況),國王或者皇帝成為分散的控制鏈條上唯一的匯合點。如果他無法行使職權、無法彌補憲法的缺失,那麼國家體系的問題則永遠無法解決,國家也不會團結。而這些君主往往都無法達到這樣的要求,或者說,他們一開始就拒絕這樣做,因為他們希望有權執行各種關鍵議題,使自己的觀點得以保留,並顯現自己的卓越。這樣的想法破壞了決策過程。當時的情況大致是:相關大臣所做的決策很容易被其同僚或對手推翻或破壞,這些大臣經常覺得很難使「他們的行為與大環境相融」。在這種疑慮下,大臣、官員、軍事指揮官,以及政策專家都認為自己有權將各自的提案納入討論範圍,而不是個人對政策結果負責。此時,人們感到必須與君主的步調一致,
於是出現相互競爭和拍馬屁的文化,這破壞了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繫,而這種聯繫能夠為決策提供更平衡的解決辦法。這樣的結果造就了派系之爭與誇張虛浮且十分危險的政治文化氛圍,以致釀成一九一四年七月的災難。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一書,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英國劍橋大學歐洲現代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洲人文學院院士。曾於2007年榮獲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他曾因對德國歷史研究的突出貢獻,被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勛章。他所著的《夢遊者》被歷史學者們公認是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把史書寫到登峰造極之境。克拉克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都像患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高估自己、錯估形勢。因此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中的大悲劇。然而至今,一戰開戰已滿百年,而戰爭依舊不斷,世人如夢遊者一般,仍舊無知於己身行為所產生的影響。